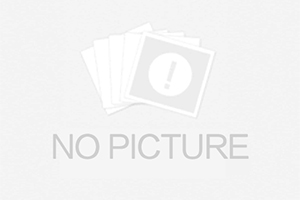1985年8月,高考放榜,我收到了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。宴请的酒席已经摆过,转户口等手续已经办完,甚至,父亲都为我准备好了一些全国粮票。
不过,还未到开学时间,我自然还得帮家里干活。
那天,我一早便把背心搭在荷叶上,光着背,赤着脚,穿着大裤衩在村后自家的藕地里摸藕。摸藕有技术,什么样的叶子下面才长藕,一般人是不知道的,但于我而言,一看就知该从何入手。不过,摸藕最大的问题是,时间长了,手指生疼,而且污泥浸染指甲后,指甲颜色会黑很久,怎么打肥皂抹洗衣粉,都洗不掉,多少天后才能恢复本色。
当我正弯着腰躲在大荷叶下费力地摸藕时,听闻田边有人唤。抬头一看,是我堂婶喊我,堂婶边上站着我同班的俩同学,陈同学和蒋同学。
陈蒋二位同学分别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了,陈的高考分数比我还高,那几日还在中学做口语强化训练。我见到他们,自然高兴,顺手抹掉手上的污泥,跨上田埂,问他们怎么有空跑我家来了。
他们说,是蒋校长让他们来请我去学校给下届文科班的师弟师妹们“传经送宝”,讲讲学习和高考经验。
我说,我哪有什么经验啊,除了下苦功,也就瞎猫碰到个死老鼠而已。但俩哥们儿不依不饶,不停催促我。我在河边洗脚洗手时,还在不停地推脱。
待我洗干净手脚,同学便不由分说,把背心给我套上,推着我回到村里,跟我父母说了句,我们走啦!便把我摁上陈同学的自行车后座,径自往学校而去。
无奈,我光着脚跟着他们走进了校园——彼时乡下光脚不稀罕,不过,光脚进校园的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不过,我的师长倒不会因为我这身打扮批评我,师长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,早已见多不怪了。蒋校长批评我的是另一个问题,他说:刚考上大学,让你来给下一届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经验,你就摆架子,推三阻四的,这么快就忘本了?
我赶紧说:忘本是万万不敢的,只是我除了下死功夫,全是碰运气,也没什么可讲的,怕误人子弟。我这话绝对不是推脱,而是由衷之言。
像我这般脑袋不灵光的家伙,只知道笨鸟先飞,肯下功夫,也实在没啥了。多年后我同班的顾同学——他跟我聊起,说当年我奶奶跟他父母说我高中复习时,蚊子太多,把双脚放在瓮头里防蚊子,摇着扇子读书。这也算是一个我苦读的侧面例证了。
蒋校长不管我如何辩白,反正来了,就得进教室去讲。我硬着头皮进了教室,就我这一身打扮,一点不像刚中举的人,学弟学妹们中有一些人跟我也相熟,看我这副行头,忍俊不禁。
站在讲台上,满是慌张。面对人多的场合,我向来怯阵,如今仍是。但箭在弦上,只得磕磕巴巴地跟师弟师妹们讲述了自己的努力,以及学习的方法,尤其是历史——我可是当年江苏省单科最高分。好不容易讲完,已是满头大汗。中午蒋校长在食堂请我们几个同学吃饭。一位同学边吃边跟我说:朱学东,你肩膀和背上的泥巴还没洗掉呢!
2013年夏天,高考正酣时,我在北京组了一个酒局,十来个人,大多是我中学同班同届或前后届的校友。陈同学也在座。
聊及正在进行的高考,回忆当年我们高考时的故事,大家各有感慨。一位低我一届的师弟——也是大学的师弟,如今在国家某重要岗位任职——端起酒杯对着我,跟大家说,我要好好敬朱学东一杯,当年他光着脚、穿着大裤衩、身上沾着泥巴,给我们讲如何复习如何参加高考,讲的内容是不是给了我帮助,我记不得了,不过,就他那形象,已经大大鼓励了我们班的同学,大家都说,像他那样满身都是泥巴的土包子都能考上人民大学,我们加把劲也行!我就是被朱学东激励,最后意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!
原来如此。